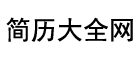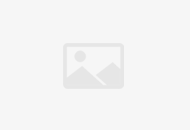马道一的个人简介
马祖道一(709-788,或688年―763年),俗姓马,又称马道一、洪州道一、江西道一。唐代著名禅师,开创南岳怀让洪州宗。史书说他容貌奇异,牛行虎视,舌头长得可以触到鼻,脚下有二轮文。谥号大寂禅师。马祖道一禅师门下极盛,号称“八十八位善知识”,法嗣有139人,以西堂智藏、百丈怀海、南泉普愿最为闻名,号称洪州门下三大士。百丈怀海下开衍出临济宗、沩仰宗二宗。简介
马祖道一,幼年依资州唐和尚(即处寂)剃染,就渝州圆律师受具足戒,开元年间至衡岳,从怀让禅师习禅。天宝初年到过福建建阳(今建阳县)佛迹岭,开始弘化授徒。不久到临川(今江西临川县)的西山,后又至虔州(今江西赣县)的龚公山宝华寺弘法28年。代宗大历4年(769年),马祖道一来到洪州(今江西南昌市)的开元寺(今佑民寺)说法,四方信徒云集洪州,入室弟子139人,使开元寺成为江南佛学中心,洪州禅由此发源。和师傅怀让相比,道一是广授门徒的禅师。怀让那一辈人如果是静修僧的话,马祖则是开宗门的一代。江西的法嗣,据史书说,广布天下,影响深远,称洪州宗(洪州禅),与青原一系下的石头宗遥相呼应,自此禅宗大盛于天下。 日本哲学、佛学、汉学大师铃木大拙指出:“马祖为唐代最伟大的禅师”。胡适称马祖为“中国最伟大的禅师”。
师承
马祖道一12岁出家,26岁时在衡山传法院结庵而住,常习坐禅。当时南岳怀让禅师住持般若寺,得知道一每天坐禅,是一个有造就的人,准备前往传法院问道一。
一天,怀让看道一整天呆呆地坐在那里坐禅,于是便见机施教,问道:“你整天在这里坐禅,图个什么?”
马祖道一答道:“我想成佛。”
于是,怀让拿起一块砖,在附近的石头上磨了起来。
马祖道一见此十分惊异,立刻上前问怀让:“师傅,您磨砖做什么呀?”
怀让答:“我磨砖做镜啊!”
马祖道一困惑不解问:“磨砖怎能成镜?”
怀让说:“既然磨砖不能成镜,那么坐禅又怎能成佛?”
马祖道一向怀让禅师请教。怀让说:“这道理就好比有人驾车,如果车子不走了,你是打车还是打牛。你是学坐禅,还是学坐佛?如果学坐禅,禅并不在于坐卧的形式。如果是学做佛,佛性无所不在,佛并没有固定的形相。在绝对的禅宗大法上,对于变化不定的事物不应该有执着的取舍,你如果学做佛,就是扼杀了佛,如果你执着于坐相,就是背道而行。所以,坐禅不可能悟道成佛。”
马祖道一闻听,如醍醐灌顶,豁然开悟。
马祖道一又问:“如何用心,才能达到绝对的最高境界。”
怀让答:“你学明心见性的禅法,如同播撒种子。而我教你的禅法要旨,好比天降甘露,只要条件关系两者契合,就可以了悟绝对本体。
马祖道一又问:“绝对本体不是物质,又不是形相,那怎样才能悟道呢?”
怀让禅师答:“明心见性同不执着于物相都一样可以悟道。心性包含一切种子,遇甘露即可萌发,即无固定的形相,也没有成功与败坏的分别。”
马祖道一跟随南岳怀让禅师参学有十年之处,后来去江西做方丈。怀让禅师去世后,马祖道一继承了他的衣钵。在怀让的六位入室弟子当中,只有他得到了心传。
生平
马祖道一的一生,依其活动地域和思想发展线索,可以明显地分为三个时期:
1.剑南时期(709~733)。中唐时期的剑南是唐玄宗时的十个节度使之一,约当今四川中部地区,下辖益、彭、蜀、汉、资、渝等州。道一幼年在本邑罗汉寺依处寂(665~736)出家。二十岁前后在渝州(今重庆)依圆和尚受具足戒。曾师从著名僧人、新罗国王子无相(683~762)。这一时期的游学,主要接受了五祖弘忍一系的影响,奠定了禅学思想的基础。
2.衡岳时期(733~742)。师从于怀让,度过了青年时代,接受了六祖惠能衡岳一系的教育。
3.江西时期(742~788)。先后住在临川(唐时属抚州)西里山、南康(今赣县田村东山村)龚公山,两地共三十余年(742~773)。唐代宗大历八年(733),移居锺陵(今进贤县)开元寺,地近洪州(今南昌),随后一直以洪州为中心广泛地开展弘法活动,创立了“洪州禅”。他去世之后,唐宪宗元和年间谥号“大寂禅师”。道一门下弟子很多,其中入室弟子依《景德传灯录》记载有139人,依《祖堂集》有88人,各自弘化一方【 吴立民主编:《禅宗宗派源流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1998年,137~139页。】。
记述马祖道一禅法的资料主要有《景德传灯录》、《祖堂集》、《古尊宿语录》、《四家语录》等。在《四家语录》卷一里收有《江西马祖道一禅师语录》(简称《语录》)一卷,是本文研究的主要依据【《?续藏》第119册,810~816页。】。马祖道一的禅法,从引导修行者达到最好修行境界的角度看,分为三个阶段,即他用了“三段论”,从“即心即佛”、“非心非佛”到最后的“平常心是道”。
心法
1、《五灯会元》卷四载:赵州从谂问南泉普愿:“什么是道!”南泉说:“平常心是道。”其实平常心之说,蕴含于《六祖坛经》而公开倡导于马祖道一。禅录载,马祖一日示众云:
道不用修,但莫染污。何为染污?但有生死心,造作趋向,皆是染污。若欲直会其道,平常心是道。何为平常心?无造作、无是非、无取舍、无断常,平凡无圣。
此中所说的平常心,究竟是什么心?据马祖所说,它是不染污的,与有造作趋向的生死心相反。从正面讲,它是无造作,无是非,无取舍,直了真圣义谛的无分别智。但它不名智而以心为名,因它是恢复了心的本来面目,而直接就是本心了。但它又不名本心,因为本心是术语,为破文字障,避免名相化,故不名本心,而从通常惯语的平常心命名,以便与实际生活水乳无间。其实它就是“涅盘妙心,实相无相,微妙法门”,是不生不灭的本体,也是般若空性、心性自然的体现,所以说平常心是道。
平常心的形象怎样呢?平常心的形象可用六祖常说的“平直”二字来说明。平谓心平,直谓行直。心平行直是禅功的成熟,也就是道,也可说就是佛心。故六祖说:“心平何劳持戒,行直何用修禅。”又说:“平直即弥陀。”六祖只从平常心的行相来说平直一词,认为那就是道,而未直言平常心是道。后来禅宗大德于此处有悟,觉察到六祖所说的心平行直,可说就是平常心,因而有平常心是道之说。平常心有体有用,就其体相说,就是心平;就其用相说,就是行直。心平的具体情景,六祖在《坛经·付嘱品》里用“一相三昧”来说明,他说“若于一切处而不住相,于彼相中不生憎爱,亦无取舍,不念利益成坏等事,安闲恬静,虚融淡泊,此名一相三昧。”心平则自有般若现起,通达任何一法,都无大无小,无高无低,无优无劣,无善无恶,无净无不净,无有少法可起分别。所分别既无,则分别心与无分别智亦无所得,而一切无分别,平等共一如,心不住一切相,惟有一清净相,相续而转,故名一相三昧。至于行直,其具体表现,应知即六祖所说的“一行三昧”相。六祖说:“于一切处,行住坐卧,纯一直心,不动道场,真成净土,此名一行三昧。”由于心平,不住诸相,如如不动,与境相接,自不起思虑分别,而随感随应,直往直来,其心仍然是清净无相,如如不动,故名一行三昧。此中一相三昧,体现心平,是从平常心的体相上建立;一行三昧,体现行直,是从平常心的用相上建立。有以平常心体相为实质的一相三昧,自会有以平常心用相为内容的一行三昧,因而反过来有一行三昧,也就必须有一相三昧。这就是说:心平行自直,行直心必平。如果用“寂照”义去理解平直义,则一相三昧是寂而常照,慧在定中;一行三昧是照而常寂,定在慧中。把这两种三昧结合起来,就是平常心的全貌。
由此,“平常心”有二个层面,即其体相上说,是不生不灭的本性;从其形态一看,则是有生有灭的现象,表现在日用中的显现。平常心就是“直心”,用平常心比讲直心更贴切。盖日常生活中,见于平常之喝茶、吃饭、搬柴、运水处,皆与道为一体;行住坐卧等四威仪之起居动作中,就是禅法。意思是说我们平常的生活就是道,而此四威仪乃为真实之禅。惠能讲“但行直心,于一切法,勿有执着”,马祖说“行住坐卧,应机接物,尽是道。”这种“直心”和“平常心”,实即是日用事中无取、无舍、无执着的心行。
我们平常有太多的造作,陷于是非人我中无法自拔,如种种攀缘、谄曲、分别,以致痛苦不堪,感到失落,心不能平衡,在感情的旋涡中回转,失去宁静的心态。所以现代人都讲要回归自然,让心处于质朴平直的状态,就是要找回一颗宁静安怡的心,以求心态达到平衡,让心处于自然状态中。这个平常心既不是我们的烦恼心、机巧心,也非圣贤们的种种胜见胜解,这颗心应该是不增不减、不生不灭、不染不净,处于中和的状态,就是当下现实之心。故平常心,是指眼前之境就是真心的显现,当下就是真理,不需要到遥远的地方追寻。
2、一天马祖升堂,对众徒说:“你们要自信自心是佛,此心即是佛心。达摩大师不远万里从南天竺来中国,传上最上乘的明心之法,目的就是要你们开悟。达摩老祖外以法衣表信,内以《楞伽经》印心。为什么要以《楞伽》印心?这是怕你们这些人颠倒,不能自知此心即是佛,不明此心各自都有。《楞伽》大经,千言万语,说个什么呢?佛语心为宗,无门为法门。求法的人应无所求。心外无佛,佛外无心。所谓的善并不足以追取,所谓的恶也不足以舍弃,这都是偏执的一边之见。无善无恶,不思善也不思恶就是净秽双遣,真俗不二。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本不实存,全由心生,心是万物的根本。森森万象,品物流杂,都是一法所派出。凡是所见的现象,都是心,见象就是见心。心不是空洞的,它因现象而展现。你们说法论道,只须随事而变,事也好,理也罢,都要无所挂碍,无所粘滞。修证菩提道果,也是如此。心所生的,就是色,色就是空。知色是空,生即不生。若了此意,方可谓之随时流转。穿衣吃饭,都是养育圣胎。任运随时,此外还有什么事?”马祖又随口念了首偈子:
心地随时说,菩提亦只宁。
事理俱无碍,当生即不生。
《楞伽经》记述的是佛祖释迦牟尼在楞伽山顶向弟子大慧解说一切唯心、万法唯识道理的经典。讲经地在锡兰岛(今斯里兰卡)。山名楞伽,楞伽为一种宝贝的名称,又有不可到、不可入之义。此山以楞伽命名,一言其至宝,一言其险绝难到。佛在这里讲述大经.以表殊法。禅宗初祖达摩菩提西来传法,即以《楞伽经》为印心法宝。大慧大士在本经中就曾向佛祖问过“宗通”和“说通”的问题。佛祖说:宗通即是自悟所达的自证自觉实相,所谓的说通,即从经典中学到的他人证悟的境界,也就是“教”。所以禅宗虽倡扬“明心见性”的宗说,也重视经典之教。通宗和通教还是两翼并用的。在达摩老祖以此经印心之前,中土即有《楞伽》译本,经达摩的提倡,不仅禅宗,其他教派中也都十分重视这部佛学宝典。
六祖之前,禅宗以《楞伽经》印心。经中有“佛语心第一”的话,所以禅宗被称为心宗。在达摩度二祖、二祖度三祖时,都有“安心”的故事。所谓的安心,即与注重《楞伽》有直接的关系。“安心”是自初祖至四祖禅法的重要特征。但随着时间发展,楞伽经师们不免穿凿附会,支解经义,从四祖道信开始,就改变单纯以《楞伽》印心的做法,也用《金刚经》、《法华经》、《维摩诘经》等法典。到六祖就开始正式用《金刚经》为印心的教典了。禅法的纲领也由“安心”,变为“无住”,即用《金刚经》的“无所住而生其心”为入道的要诀,方法更加切实具体。所以禅宗虽从一开始就标榜自己是“宗通”,即与“说通”相对的“教外别传”,它也是要用“教”,要用“说通”的。
马祖道一讲的这一席话中“佛语心为宗”,很明显即“佛语心第一”的翻版。但区别是,“佛语心为宗”确证的是六祖以来的“无住”法门。换言之,是在以《楞伽经》,解《金刚》无住法。由此也可以看出,道一禅师也是一位研习佛典的人物。马祖的这一席话,中心是一个“信”字,信什么?信自心,信自家佛性。“恐汝颠倒,不自信此心之法”,是直说大义的用心良苦处。在这里我们仍可看到六祖禅法朴素的遗风,这也正是这位禅宗大师开宗立统的成功之处。与后世禅师用棒用喝相比,马祖的方法更加朴素,他对信徒自信心的热切的鼓舞,要比堵截式的棒喝更能提高士气,具有更普遍的推助力。三祖僧璨曾作影响深远的《信心铭》,马祖此处的苦口婆心,就是同一种古道热肠了。
3、止小儿哭
马祖讲过这一番大道后,有和尚出来质疑,说:“和尚凭什么说心即是佛?”老师讲完,学生不服的出来辩驳,这是佛家的习惯和风气。这是一种平等关系,师的尊严不在面子上,而在道上。
马祖回答:“我说这句话,是为止小儿啼哭。”小孩子哭闹时,大人总要拿点什么哄他止哭,即心即佛的话头也是在哄你们不哭。
“那小儿不哭时又怎样?”僧问。
“非心非佛。”马祖答。
“非心非佛”和“即心即佛”是对立的,但却又是统一的。人人相信自心是佛,也就不存在什么身外心外的佛,这就是非心非佛了。这是一种辩证关系。
那僧人又问:“除了哭的和不哭的两种人,第三种人来,你如何指示他呢?”
“能向他说的却不是物。”马祖说。意思是,说就不是,不可言说。世上除了明白“即心即佛”和“非心非佛”的两种人,还有什么人呢?只有与佛契合的人,这样的人已超越了真俗对立,还须向他说什么呢?
“那哭与不哭的两种人中的一种来了,你又怎样指示他呢?”僧问。
“让他自己体会去。”马祖答。
又问:“什么是祖师西来的用意。”
“那眼前的又是什么意?”马祖的意思是说,祖师意和现在的意有什么不同吗?没有,既然非佛非圣,哪还有什么祖师不祖师的区别!
4、赏月勘徒
马祖门下,百丈怀海、南泉普愿、西堂智藏是其得意弟子。
有一天傍晚,师徒四人在一起看月。师问:“正这样的光景怎么样?”
西堂答:“正好供养。”
百丈答:“正好修行。”
南泉则拂袖而去。
马祖说:“智藏是参读经的主儿,怀海是位禅家,只有普愿,超然物外。”
马祖曾问百丈怀海:“你用什么方法开示人?”
怀海举起手中的拂子。
“就这个吗?”禅师问。
百丈又把拂子扔掉,算是回答。
在以动作、物件开示人的一派禅师手里,拂子有很多用场,表达的意思也因时因地而异,这在以后我们会看到。在拾得和尚的故事中,我们曾见他用叉手而立、扔下扫帚等动作回答别人的提问,百丈和尚此处的举拂、抛拂,方法大体与拾得一样。
马祖问他什么法?这“法”自然“说是一物即不中”,所以就举拂,举拂子是一种动作,是有所为,故可表示有为法。意思是说:总要教些什么。马祖再问,抛下拂子,这是无为法。有教是一法,不教亦是一法。但不论有、无,对象都是一杆拂子。不论有为、无为,拂子还是拂子,它都是不变的,是超出有无的,也就是那个不可言说的“一”。可以教什么呢?就是这个一。百丈不落言拴、理路地回答了师傅的提问。
又有一位和尚问:“如何是达摩祖师西来之意?”
马祖听罢举杖就打,边打边说:“我若是不打你,大家会笑我的!”这是以棒喝的截断方法回答问题,在说法的方法中属“巧说”。道一不仅是朴素的直说派,也有巧说,直说巧说结合,成其大师风范。当头一棒,寓意和前面反问“眼前是什么意”内含相同。都是在说,这问题不可问,不可答,不该问,不能答。打你才是帮你,否则会让人笑话的。
5、石头路滑
禅宗的注重践行体证,不仅限于参悟,而且也包括游学多师,开阔心智。这叫行脚。有位小和尚,名叫耽源,行脚回来见马祖禅师。在师傅面前画了个圆,站在上面向师傅行礼。师傅看了纳闷:“你敢莫是要做佛了?”禅宗用圆表示妙谛圆融,站在圆里,自然是成佛的样子。
小和尚回答:“我不知道给这捏造个什么名目才是。”试想如果耽源说出这是什么或不是什么,是否要挨棒子呢?马祖听完说:“我不如你。”
小和尚也不置可否。马祖门下,龙象成群,于此可见一斑。
有位叫邓隐峰的僧人,向师傅辞行。马祖问他:“什么地方去?”
“去石头希迁禅师那里。”隐峰答。
“石头路滑,不是好去的。”马祖说。
“竿木随身,逢场作戏。”隐峰信心十足。临济禅师有四喝,其中有“有时一喝,如探干影草”,故“竿木”有探虚实之用。隐峰是想和石头希迁周旋一番,探探他法力的虚实。
不想邓和尚才到希迁处,便给石头“滑倒”了。隐峰到了希迁禅堂,绕着禅床走了一周,把手里的锡杖敲得山响。问:“是何宗旨?”
石头也不作答,只仰头叫道:“苍天!苍天!”隐峰无语。回到马祖大师处把情形说了。马祖说“你再去一次,等他一有反应,便嘘他两声”。
师傅面授机宜,隐峰便又去了。再问是何宗旨。石头听罢嘘了两声。本来师傅是要隐峰嘘的,现在被人抢了先,又没了法子,便又回到师傅这里。马祖笑了笑,说:“我已告诉过你,石头路滑。”
苍天无语,但也有语。孔子说天何言哉,四时行焉,是无语中有语。石头喊苍天是有语中无语,苍天虚空,容摄一切,以此显出隐峰问话不当,是答而不答,不答而答。隐峰在马祖弟子中属不善机锋的人,一句“苍天”就让他逢场无“戏”可做。马祖让他嘘两声,嘘与虚同,是让隐峰用虚空破苍天、但石头是有大机锋的人,隐峰回转,下次再来时,身后藏的是马祖,这一点他怎么会不知?石头路本来就滑,再遇上个脚底没跟的,所以连马祖也是“帮腔上不了场”了。
6、钝根僧人
有位讲僧――也就是以讲经为业的僧人――来参拜马祖。问禅师:“不知禅宗传承的是什么法?”
马祖反问:“座主传承的是什么法?”
“不才忝讲经论二十余本。”讲僧答。
“莫不是狮子儿了吗?”马祖说。这是在恭维对方,佛家常以狮子比说法力雄威的人,狮子一吼百兽脑裂。
“不敢当。”讲僧谦让。
马祖便嘘了两声。讲僧一听,说:“这是法。”
“是什么法?”马师问。“是狮子出窟法。”讲僧说。
马祖默然。
讲僧说:“这也是法。”
“是什么法?”
“是狮子在窟法。”
马祖问:“不出不入,是什么法?”讲僧说的都是狮子动静之法,不动不静的法又是什么?
僧无言以对。
于是讲僧告辞出门。转身之际,马祖叫:“座主!”
讲僧回头。马祖问:“是什么?”
僧还是无言以对。
马祖道:“这个钝根的家伙。”
讲了经论二十几部,却机锋败北。知识不等于慧识,知识是死学问,慧识是生命力。讲僧只懂可思议的,能言说的,他只能分别是什么,不是什么,对超出是与非相互对立的超越之物,便只能迷惘无措了。知识、学问只是他家本事,转化成智慧,开掘自己内在的生命创造之源,才能是真狮子,在窟、出窟,不失自性。马祖试图在讲僧迷茫而去时再给他一个机会,令其开悟,但失败了。“想阴”灾难深重,去佛最远,于此“钝根阿师”又见一例。
7、日面月面
马祖开法几十年,入室弟子一百三十余人。这些人离开师傅后,各主一方,大唱宗风,变化无穷。唐宪宗贞元四年的正月,马祖在建昌登石门山。在山林间漫步时,见洞壑平坦,心生爱意,对身旁的人说:“下个月我的这把老骨头就要到这里来了!”回到寺中后,就显出病症来。病中有一天,马祖大师突然表现得不安,院主就问:“和尚这几天尊候如何?”
“日面佛(寿命为1800岁),月面佛(寿命只有一昼夜)。”马祖回答。
这是马祖灭前留下的最后一则公案,后人多有参解。有人用左眼是日面佛、右眼是月面佛解释,《碧岩录》说都是“没交涉”,不相干。有位尼总持重病,作颂:“气绝绝精绪,举意意无路,瞬目尚无小,常年不出户。”颂被一位芙蓉道楷禅师见到,说:“只此一颂,自然绍得吾宗。”是说此颂有马祖当年日面佛、月面佛的禅境。人在死之将临的病中,万念寂然不起,只有生命的本能在动,是最易由此自见心性的,马祖的“面佛”或许就说的是这种境界。
宏智正觉禅师亦曾作过一偈:“日面月面,星流电卷。镜对像而无私,珠在盘而自转。君不见砧锤前百炼之金,刀尺下一机之绢。”铁锤在铁砧上百炼金钢,刀尺裁织下一机绢帛,这是说马祖大师在病中还总是那样不忘做功夫。那马祖大师为什么“不安”呢?马祖大师虽是面佛,不是求佛,但生死之际总是佛观佛现,感到自己未能自主。这时实在需人夺境不夺人的一声断喝,但院主却不是那样的人选。
到二月一日,马祖道一洗头沐浴,之后跏趺而灭。只要活的明心见性,随缘任运,不管是长寿还是短寿,都不虚度此生。